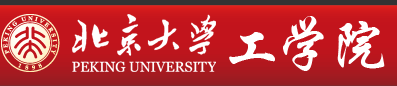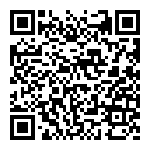采访手记:这是一个普通的老人,历史的车轮滚滚里,过着平凡人的生活,被社会大潮向前推着走,求的是现世的安稳,谈不上建功立业的宏伟梦想,也不为豪言壮语所驱。他正常地结婚生子找工作,寻求舒适的生活,没有大篇的人生道理,也没有对苦难的不堪回首,不过笑谈几句罢了。在久经了岁月的洗礼之后,享得儿孙满堂,合家幸福,对他而言,就是一种圆满。
但是,他,和从那个时代走过的很多人一样,是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人。他们以个人所学,投身建设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,义无反顾。这是那一代人的特质:国家要求至上,理所当然。他,及他们,值得被记住。

王登五
王登五,河北人,家在北京,1940年进入北平大学学习,在建筑系学习一年后转入土木系,1944年毕业。今年已91岁高龄的王登五,依旧精神矍铄,每日读报散步,始终笑呵呵的,一副乐观豁达之态。
1940年的北京已是沦陷区,皇城根下的北京人生活在一种压抑的平静之中。当时北京多数高校为日本人管制,没能跟随大部队前往后方的年轻人,不得已在日辖区读书。王登五就读土木系,也几经了辗转。他本是考取了北大医学院,哥哥担心他粗心,不建议他学医,错过了医学院的入学。考虑到自己喜欢四处走走,不喜欢死读书,王登五选择了土木系,想着可以去修铁路,也就能到处游历,到处看看。
在王登五的回忆中,当时的学校生活乏善可陈,不像今日有诸种的文娱活动,只是偶尔和同学打打篮球。亡国奴的身份下,学生读书都很刻苦,设计画图,都要熬至深夜。教书的先生中也有很多杰出学者,如朱兆雪、黎锦炯等。王登五讲起朱兆雪先生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的事情,还满是敬佩,说先生教书时就很有特色,一连讲三个小时不休息,听者众多。他印象更深的是“刷课”,当时工学院有一名教水力学的日本教员,每逢此课,同学们往往想办法“刷课”,以达成一种抵抗。每忆及此,老人脸上都露出一副恶作剧般的笑容,犹如重返青春年少。
彼时的中国,风雨飘摇,亡国的危机近在眼前,年轻人也多有惶惑之感。毕业之后的王登五,从沦陷区出走,携家带口赶了4天的路,奔至陕西,历尽艰辛,在陕西西南洛河中学谋得一份教职,教授中学数学。一年后,王登五有机会前往兰州铁路局,担任工程师,修建天兰铁路,自此,一生不离铁路事业。
时代变局下,人难寻安稳,需要随时听从国家召唤。在之后的岁月里,王登五从兰州转至太原铁路局,不久又参与修建成昆铁路。成昆铁路建设完成,周总理提出要加强沿海铁路建设,王登五又跟随组织于1967年返京,遂一直在北京铁路局工作。除了年少想四处走走的念头,在王登五眼里,修铁路更是一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事情。积弱积贫的中国,铁路事业刚刚起步,远没有今日发达,在王登五看来,能够修建铁路,是造福国家的大事业。如他所欣赏的詹天佑,以一己之力证实了中国人的能力,那是值得骄傲的。
多年的铁路工作中,修建成昆铁路的经历至今让王登五印象深刻。成昆铁路沿线地质情况非常复杂,“需要桥隧相连,山里头转几个圈再出来”,苏联专家当时都说不好修,但成昆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,涉及攀枝花钢铁的开发,修建又非常迫切,毛主席亲自下指示,希望工程可以抓紧。当时的技术水平并不先进,有很多需要人工完成的工作,如开山时工人使用刚风钻和水风钻两种,水风钻慢,刚风钻快,但刚风钻会产生很多粉末,吸入多了会得肺病。为赶进度,很多人使用了刚风钻,后期才要求大家使用水风钻。王登五回忆说,整个修建过程中,牺牲了很多人,当时每一个车站前就有一座陵园,死去的人随即就被装入一幅幅棺木,埋在陵园中。今日听来,也让人唏嘘感慨。
九十余年的人生,足够经历共和国建设中的大小波动,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。王登五参与过如成昆铁路这样的建设工程,也参与过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。他当过造反派,也挨过批斗,蹲过牛棚,但老先生并没有多讲。人生行至此时,也许已经看淡了很多东西,回想起来荒唐的过往,王登五笑着说:“现在想就是年轻吧”。
安享晚年的王登五,依旧每日看《参考消息》,关注国家形势。他留恋昔日北京城的幽幽古迹,也感叹今日城市建设的灼灼光彩,虽年老仍对这个国家的建设满怀热忱。作为工学院的老院友,王登五也一直关注着北大工学院的发展,他为院友会上学院的发展报告而深感激动,期盼学院再现辉煌。